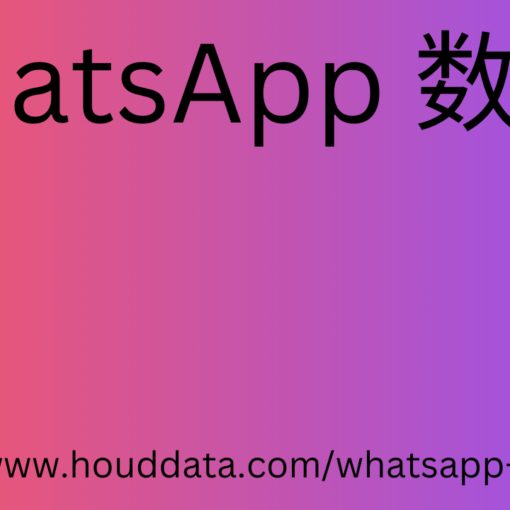当水开始从靠近我办公桌的遮阳帘的一角滴落时,我注意到了漏水。我拿来一个水桶和一个梯子,把遮阳帘倒进水桶里倒掉脏水,然后拧开遮阳帘,把它取下来。我把水桶放在地板上,抬头一看,发现天花板上有一个洞,雨水从里面漏出来。我想,这就是特朗普时代的第一天。我停下写作,去商店买了一些香烟,又开始抽烟了。
那年夏末,一位朋友从加拿大打来电话,预测特朗普会赢得大选,并邀请我如果真的获胜,去看看这里的民主。我点了一支烟,给她打电话。我想在 1 月份离开美国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那时我能去吗?我说我家天花板上有个洞。挂断电话后,我买了一张飞往多伦多的机票。机票不贵。大多数人如果可以的话,不会在 1 月份前往安大略省。
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现实,但可以承受大量的真人秀
《两个头的东西》中充斥着追逐戏和关于种族主义的笑话,但在此之前,它明确表示,像米兰德的富有外科医生这样的人认为,只要能让白人活下去,让他们更接近永生,对黑人进行实验和杀害是可以的。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在这个国家真实发生过。《两个头的东西》在全国各地的露天汽车影院和电影院首映的同一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故事被《纽约 时报》曝光。
WhatsApp 号码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whatsapp 数据 消息号码之一。通过WhatsApp号码可以非常快速地与客户沟通。 WhatsApp 号码可用于改善营业地点。可以使用 WhatsApp 号码增加企业客户。任何公司的营销工作都可以通过使用 WhatsApp 号码来加强。
四十五年过去了,情况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乔丹·皮尔的《逃出绝命镇》在总统就职典礼一个月后首映,它对《两个头的怪形》进行了更新,取消了被砍下的头颅,使“凝固物”成为一种只需进行脑部手术即可实现的思想融合。在皮尔的电影中,白人为延长自己的生命,完全寄居在一个年轻黑人的身体里,并控制了头部等所有部分。这个身体无法拒绝占据它的思想,无法与之争辩或打它的脸。两者融合在一起,黑人意识从影片的“凹陷处”向外凝视,一动不动,沉默不语。与《两个头的怪形》不同,《逃出绝命镇》将《反抗者》与《不死之脑》分离。
格里尔在《双头怪形》中饰演的角色,在死牢中,已经注定要被处死。这部水门事件时期的夸张的社会政治恐怖片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将民权斗争的冲突真实化,要求观众认真对待它,同时又邀请他们嘲笑它。从那时起,这部电影就一直处于严肃评论的水平以下。然而,由于特朗普的头,它突然对我们说话了。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也就是 1989 年,当时他还只是个有钱的饶舌者,一个讨厌的人,特朗普在《纽约时报》上买了一则大广告,公开呼吁处决“中央公园五人组”,这五个年轻黑人男子被指控并被判犯有袭击和强奸罪。2002 年,这五个人因 DNA 证据被宣告无罪,并从监狱获释。他们起诉纽约市,并以 4100 万美元和解。去年,特朗普不遗余力地让选民知道他仍然相信他们有罪。这就是他茁壮成长的方式。现在,他已经把自己的头嫁接到了我们这个集体的身体上,他那恐怖电影般的发型总是在我们面前。特朗普的头脑正在努力控制我们的行为和反应,就像米兰德的头脑在这部廉价电影中努力控制格里尔的身体一样。魔鬼在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两个头的东西》太愚蠢了,詹姆斯·鲍德温在他关于种族和电影的长篇论文中没有注意到它,我不得不去加拿大才能看到它。如今,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种愚蠢的事情。
像山一样思考
从上海到孟买到凤凰城,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的隔离已经超越了灭绝和隔离。即使我们在自身之外遇到的事情也缺乏汉娜·阿伦特所说的行动的力量:开始新事物,推动事件发展。宠物的剧本经过严格编辑,以确保安全、卫生,符合刻板印象。工业化农业已经对它所食用的动物实现了极权控制。没有掠食者会找我们的麻烦。
伴随着全球驯化,一种相反而可怕的潜在现象正在酝酿。每一次新的超级风暴、传染病或年度高温记录都预示着厄运,对世界穷人的影响最为严重,但最终几乎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深刻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但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自然界也成为人类活动更稳定、更可替代的背景。然而,整个世界似乎也准备向我们袭来,就像一群刚刚改变立场的愤怒的神灵。
对于作家来说,这个奇怪的世界 —— 驯服至死、野性如野猪 —— 激发了他们对非人类行为、能动性和意识的迷恋。在高级学术文化中,文学学者对风暴和树木的能动性大加赞赏,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态形式,也是一种社会形式,社会理论家则概述了跨物种的民族志和联盟。但像往常一样,学术趋势只是密涅瓦猫头鹰的猎物。更有力的情绪证据是雄心勃勃、通常很出色、有时很荒谬的写作,从散文、回忆录到科普,它们执着地问:是什么在通过其他物种的眼睛回望着我们?我们能摆脱自己的头脑,了解鹰的视角吗?有没有像山一样思考的东西?
那些刚刚熟悉大学文学课程的人会直观地理解这一区别,即使大多数 40 岁以下的人对“制度化的审美教育计划”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于那些不属于学术界高额付费墙的人来说,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简要版本大致如下:体裁、风格和叙事的变化使文学成为抵抗、压迫和边缘主观性的特殊记录。这就是文学的价值。有时文学文本会排除或隐藏这些声音;有时,它会无意或有计划地放大它们。对文本时期的研究可以揭示其潜在或明显的政治含义。因此,学术或批评的工作(两者的混合是诺斯诊断的问题的一部分)就是展示文学中和通过文学对具体和专属政治欲望的编码。
我们太过于人性化,无法知道非人类世界会有多大的文化性、多大的意图、多大的意义。
其他书籍则试图从理智的角度拉近动物之间的距离。在一项针对大众的调查中,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 (Frans de Waal) 提出:“我们是否足够聪明,能够知道动物有多聪明? ”而科学作家珍妮弗·阿克曼 (Jennifer Ackerman) 则在一本提出但无法回答诸如园丁鸟是否具有审美感等问题的书中赞扬了《鸟类的天才》。海洋生物学家哈尔·怀特黑德 (Hal Whitehead) 和卢克·伦德尔 (Luke Rendell) 为我们可称之为“鲸鱼和海豚的文化生活”的东西提供了更枯燥、更科学的证据,包括虎鲸的食物禁忌、鲸鱼歌曲的创新和变化,以及父母对简单工具使用方面的指导。在这些调查中,有一些真正令人难以置信时刻。在《超越语言:动物的想法和感受》中,生态学家卡尔·萨菲纳 (Carl Safina) 描述了大象如何温柔地对待死者的骨头,从这种行为中,人们几乎不可能不承认它们有着共同的经历。 (你可以在 YouTube 上看他们怎么做,也许你应该看看。)不过,大部分情况下,认知壁垒仍然存在。我们太过人性化,无法知道非人类世界可能有多文化化、有多有意图、有多有意义。
只有“硬”科学才可以免于解释其幻想。德国林业学家彼得·沃莱本 (Peter Wohlleben) 在畅销书《树的秘密生活》中从经验惊喜开始。树木通过根系交换养分,使邻居在压力和疾病中存活下来,有时还能维持一棵一百多年前被砍伐的树木的光秃秃的树桩和树根。当害虫侵袭时,它们通过根系和空气发出化学警报。一些应急化学物质会刺激邻近的树木释放保护性驱虫剂,而另一些则会吸引捕食者来吃掉害虫。营养交换和化学信号都得到了真菌的极大促进,真菌生活在森林根部,传递营养和信息,就好像它是一个混合的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
文化对树木的关注往往集中在非凡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体上:英国教堂墓地的紫杉比教堂古老得多,据推测与前基督教仪式有关;什罗普郡博斯科贝尔庄园的皇家橡树,未来的查理二世在 1651 年伍斯特战役中战败后,躲在它的树枝下躲避圆颅党;或者新泽西州伯纳兹的六百年老橡树,当地传说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在这里休息。对神树和统治者之树的依恋是一种思想的残余,即万物都是按等级制度排列的,每个自然领域都有自己的领主,每个领主都承认其他领域的领主,就像人类统治者在他们的王国中所做的那样。
换句话说,生命形式首先必须平凡,才能支撑真正的奇妙。
经常走小道的人,就像语法使用者一样,不太可能会 影响企业利润的 5 个创业错误:让我们看看什么是不该做的 觉得它令人惊讶。切罗基小道穿过的土地形状在创世神话中有所体现;这些小道还将东南部的所有切罗基人定居点连接在一起,就像罗马道路连接步行国家一样。走在这些小道上,可能会让人想起一个怪物的故事,它的垂死之战形成了一系列山峰,尽管步行的目的可能是贸易、外交或只是一次参观。
换言之,生命形式必须首先是平凡的,才能支撑真正的奇幻。简单的惊奇感往往部分是异国情调,是将不理解与欣赏混为一谈的乐趣。我们育儿室里的动物寓言集是自然界如此令人愉悦的墓志铭,因为它们故意将动物与卡通片融合在一起;地球让野兽的生命周期与晚间娱乐的时间表相一致,让它们的行为符合我们的审美。钦佩证实了我们与它们的距离。
摩尔很少表现出探索者对超越自我的渴望(因此有时能给予他人更多的空间),他最生动地描写了其他物种和前工业时代基于地点的文化。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他只能说,选择职业就像选择一条路,走一条路就像理解世界,因此路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公平的,但不如这本书的其余部分令人满意,因为实际上,改变职业,或在去 Lyft 打车的路上在熟悉的机场售货亭停下来喝杯咖啡,感觉与他在其他地方描述的略带魔力的小径完全不同,这些小径的连续性暗示着世界本身的统一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类型的小径对我们来说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
所有这些作家最终都没有完全宣称与非人类世界的联系,而正是这种联系首先吸引了他们创作的主题。真正超越自我的力量总是在别处 —— 在农民社区、在盖尔语中、在文学狂热中。至少对我来说,这些流离失所和犹豫不决令人失望,尽管我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
毁灭方法的标记
实际上,一个人对文学研究的看法,或对文学研 asb名录 究应该是什么样子,往往取决于他上过哪所大学。在一所大学的想象中,某些人物比另一所大学更引人注目。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研究史必须包括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华·赛义德;在耶鲁大学,文学研究的谱系需要考虑从威廉·维姆萨特到哈罗德·布鲁姆和保罗·德曼的过渡。目前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几乎没有人愿意声称这些祖先人物有影响力,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影响是狡猾的,很少是直接的。但即使是完美的谱系,也不意味着这些人物所信奉的方法和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事实证明,没有人真正衡量过对如何阅读文学的理解在整个文化中传播的准确性或有效性。现代语言协会并不拥有阅读实践的专利或垄断权。变异经常发生。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大多数人最深厚的阅读习惯是在中学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在大学里。
想象一下,一部“文学研究的人民史”就像托尔斯泰和司汤达所描绘的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战役一样平淡无奇、反英雄 —— 一部意图复杂、人们真诚的编年史,一百个高中教室里充斥着青春期的荷尔蒙、误解、怪人、应征者、平庸之辈,每有一位 J. Hillis 或 DA Miller,就有两百个 Lucky Jims 和 Janes。与参加会议、教职工会议和考试所花费的无数时间相比,这些辉煌的时刻 —— 新学校和新阅读方式的创立 —— 将不那么重要。它将有点像流行病的社会史,重点描述接触和传播的多个点和途径,以及促进或阻止传播的条件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