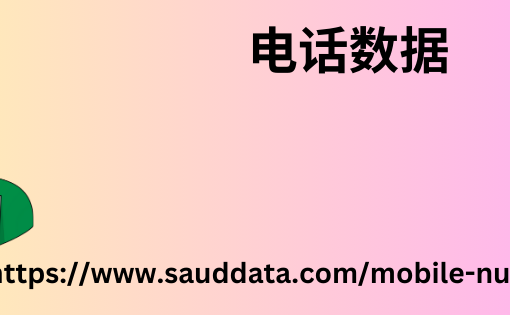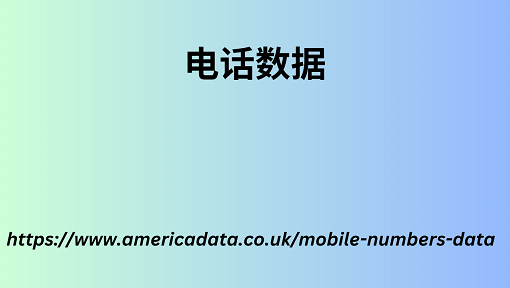政治学家史蒂芬·列维茨基和丹尼尔·齐布拉特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特朗普公然拒绝“党派克制和公平竞争”,对“我们的宪法制衡体系”构成了生存威胁。政治学家布伦丹·尼汉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特朗普不会受到“两党政治规范”的约束。彭博社的弗朗西斯·威尔金森从将民主制度描述为建立在精英两党友善基础上,转变为将民主等同于对国家安全局的尊重。威尔金森写道:“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将像对待共和党对手一样对待强大的民主机构。看看特朗普对待美国情报机构的态度就知道了。”将中情局尊为民主典范是一种更普遍趋势的表现——即使是最公然反民主的美国政治机构也被认为体现了民主。
派对犯规
那民主党呢?他们能阻止这一切吗?我们甚至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求助,恳求他们拯救我们的医疗保健、拯救我们的公民自由 —— 不要再把事情搞砸了。但我们没有多少信心。特朗普是个白痴和小丑,本应是个容易被打败的人。看着民主党输掉比赛就像看着一个自鸣得意的网球选手因为双误丢掉一千个盘点。自 11 月以来,民主党一直在努力寻找可以归咎的人。科米、俄罗斯人、剑桥分析公司 —— 似乎任何人都可以,但就是不能责怪自己。
电话号码数据库对于商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电话 电话数据 号码数据库。电话号码对于改善企业营销工作有很大帮助。可以通过电话号码直接与客户联系。可以通过电话号码来改善营业地点。可以通过电话号码通过短信联系客户来交付产品。
啊,民主党。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了如指掌。他们是我们最接近的政党。是的,他们代表了起草法案的强大商业利益。是的,他们几乎和共和党一样受游说者的束缚。是的,他们成功通过了前几届共和党政府只能梦想的立法:福利“改革”、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的,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入侵伊拉克,后来又在将敌意转移到俄罗斯时,又陷入了悲观的反悔。是的,他们是测试和特许学校、健康保险集团和制药游说者、大学私有化和虚假精英统治、去工业化和专业精英利益的政党—— 或者他们 不是。是的,他们似乎无法支撑一个坚定的句子,而不会让愚蠢的迂回曲折之风吹倒它。是的,他们似乎对对句修辞手法(“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多样性的力量,以及我们优势的多样性” )有着咬牙切齿的喜爱。是的,是的——是的。但是……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把民主党从数十年的右倾中拉回来吗?对于左派来说,这是一个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问题。基思·埃里森 (Keith Ellison) 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给我们带来了短暂的希望:当伊丽莎白·沃伦 (Elizabeth Warren)、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和许多工会组织支持他时,民主党似乎终于回心转意了。但随后奥巴马任命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 (Tom Perez) 来阻止埃里森浪潮 —— 这是一个让我们的希望冷却的信号。共和党的霸权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与民主党合作,至少目前是这样,甚至让他们更接近我们。问题是如何做到。
叙利亚灾难
简单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人类、社会和环境灾难,堪比 20 世纪最严重的冲突。叙利亚战前人口只有 2000 多万,但战争却造成约 50 万人死亡,200 万人受伤。自 2011 年冲突爆发以来,叙利亚人的预期寿命下降了 20 多年,从大约 79 岁降至 56 岁。该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被迫离开家园,其中包括约 60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近 500 万难民。他们的迁移反过来又加剧了欧洲和北美的政治动荡,右翼民族主义者发起运动反对据称危险的难民涌入。对政治敌人和被俘士兵使用酷刑的情况非常普遍,尤其是阿萨德政权。许多难民表示,他们女性家庭成员被强奸的风险急剧增加是他们离开的主要原因。
此外,这个有着强烈民族认同感和宗教宽容传统的国家——包括十几个基督教教派和德鲁兹派等神秘教派——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激烈宗派暴力的地方。阿勒颇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该地区的建筑和文化瑰宝之一,如今大部分地区已沦为废墟。2016 年 12 月,在俄罗斯空袭和伊朗地面部队的支持下,政府军对叛军不断减少的领土发动了最后的决定性攻击,许多居民被困在推特上,开始道别。在一段视频中,一位老人在一条被炸毁的街道中间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一边用手捂住脸,一边喊道:“我们快饿死了。什么都没有。”
战争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很难找到可行的前进道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这场冲突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魔方是愚蠢的,因为复杂性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处理魔方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扔到墙上。中东地区内外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决定,通过军事手段升级战争是合理的,因为它们认为这关系到国家利益的一小部分。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卡塔尔、中国、法国和英国都向这场冲突投入了军事资源,不仅增加了战争破坏力,还延长了战争的持续时间。如果这场战争真的需要发生,它应该是一场由双方用有限的军事资源进行的内战。相反,这场战争已经演变成一系列资金充裕的代理人战争,涉及两三个不同的方面,而这些战争都与政权对政治集会和言论的容忍度问题没有任何有机联系,而正是这些问题引发了这场冲突。虽然要求各国停止追求国家利益是没有用的,但这些国家为了追求这些利益而轻易诉诸军事手段的做法令人感到羞耻。在这个最后、绝望的阶段,需要的回应既不是反阿萨德,也不是反伊斯兰国,甚至不是反帝国主义——而是反战。
野兽离开
帕姆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我们从未发生过性关系。我们从大学开始就关系密切,在我们的友谊中,我们每天都会通电话 —— 我们就是这么亲密。帕姆非常有魅力。我想说,就吸引力而言,她和我是同一级别的,大多数认识我们的人都不相信我们说我们从未做过。为什么?他们问。我们通常开玩笑说,这是因为她是棕色皮肤,我是白色皮肤,她的父母会为此而抓狂 —— 你知道吗?这几乎是事实。我的意思是,帕姆的父母爱我,别误会我的意思,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约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达利瓦尔妈妈和爸爸就是这样的老派。
所以我想种族主义让我们分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 主数据管理最佳实践:有效数据策略指南 不说种族主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帕姆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真的不想再和她在一起了。我从来没有真正幻想过她 —— 至少,自从她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那是差不多四年前,一年前她嫁给了一个好黑人男孩。当然,我参加了她的婚礼,那是奇怪的一天。没有不尊重维克的意思,但帕姆可以做得更好。说实话,我很长时间都不喜欢维克。但不管怎样。这是帕姆的选择,我最终尊重他的选择。
不管怎样,有一天,我站在厨房里,在电话里向帕姆抱怨。抱怨我的工作。一如既往。
帕姆说:“听你谈论工作真的很不愉快。感觉就像是纯粹的消极情绪。”
帕姆会对我说一些话,如果是别人说这些话,我会变得非常防御,但和她在一起,我就能泰然处之。
所以我想种族主义让我们分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说种族主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帕姆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真的不想再和她在一起了。我从来没有真正幻想过她 —— 至少,自从她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那是差不多四年前,一年前她嫁给了一个好黑人男孩。当然,我参加了她的婚礼,那是奇怪的一天。没有不尊重维克的意思,但帕姆可以做得更好。说实话,我很长时间都不喜欢维克。但不管怎样。这是帕姆的选择,我最终尊重他的选择。
老阳台
维诺德·库马尔·舒克拉 1937 年出生于印度中部小镇拉杰南德冈。他在当地学校上学,后来在贾巴尔普尔上大学,主修农业科学。他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拉伊布尔的英迪拉·甘地农业大学任教,1996 年从该大学副教授职位退休。他的专业是农业推广,包括前往周边村庄,让农民了解新的农业技术。
《老阳台》描述了他与马克思主义诗人加贾南·马达夫·穆克提博德 (1917–1964) 的会面。这位老诗人建议舒克拉将他的诗寄给一本他认识的编辑的杂志,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舒克拉的第一本诗集是一本 20 页的小册子,名为《几乎向印度致敬》(1971),讽刺的标题使他成为印地语诗歌的新声音。其中一些诗后来被收录在他的第一本全长书《那个男人穿上新羊毛大衣,像思想一样远去》(1981) 中。舒克拉在一首诗中写道:“除了这里的一切,我一无所有。”舒克拉的“这里”是一个特定的地方:赖布尔,之前是拉杰南德冈。
舒克拉创作了多部小说,其中三部已被翻译成英文,分别是《仆人的衬衫》(1999 年)、《墙上的窗户》(2005 年)和《曾经开花》(2014 年)。舒克拉以细致入微的细节描述了中下阶层的生活及其礼仪。每一个动作或一闪念都显得平淡无奇。
云中幽灵
“我 确实打算让我的父亲复活,”雷·库兹韦尔说。他站在储藏 asb名录 室昏暗的灯光下,在成堆的纸板箱和长方形塑料箱的映衬下,他的身材显得矮小。他戴着有色眼镜。他六十多岁,但灯光、姿势、突出的肚子都让他看起来更老。库兹韦尔现在是谷歌的工程总监,但这部纪录片拍摄于 2009 年,当时人们仍然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对未来有着古怪想法的孤独幻想家。储藏室里的箱子里装着他父亲生活的遗物:照片、信件、剪报和财务文件。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收集这些文物,并将它们存放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牛顿市家附近的这座坟墓里。他拿出一本写满父亲笔迹的笔记本,向镜头展示。他的父亲于 1970 年去世,但库兹韦尔相信,有一天,人工智能将能够利用这些纪念品和 DNA 样本来复活他。“人们确实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活在他们留下的创意作品中,”他若有所思地说,“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收集所有这些振动并将它们带回来。”
库兹韦尔承认,技术距离起死回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希望看到父亲复活的唯一办法就是活着看到奇点 —— 计算能力达到“智能爆炸”的时刻。库兹韦尔等超人类主义者认为,到那时,与这项技术融合的人将经历彻底的转变。他们将成为后人类:永生、无限、面目全非。库兹韦尔预测这将在 2045 年实现。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和我们这些幸运地活到本世纪中叶的人一样,将实现永生,而无需尝到死亡的滋味。
在圣经学校,我学习了时代论神学的一个分支,该分支将整个历史划分为上帝揭示其真理的连续阶段:纯真时代、良心时代、政府时代…… 我们被告知,我们生活在恩典时代,即倒数第二个时代,它先于那个辉煌的顶峰——千禧年王国,那时乌云散去,基督再来,生活将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但我不再相信这样的未来。比起上帝之死,我更哀悼的是这种目的论叙事的瓦解,这种叙事将整个历史设想为一条弧线,坚定地朝着最终救赎的时刻弯曲。这种损失甚至破坏了我对时间的主观体验。我的时间变成了非时间。日子似乎解体了,又回到了原点。